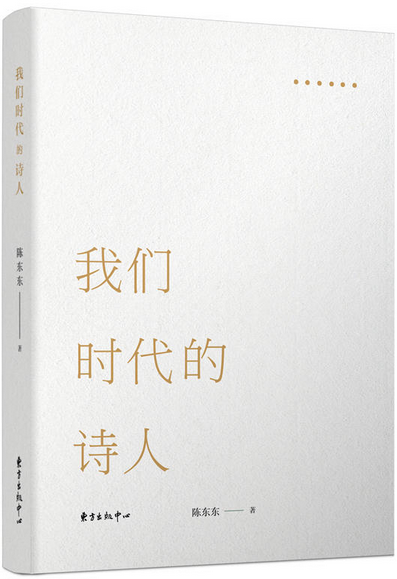
我们时代的诗人
东方出版中心
2017年4月
《我们时代的诗人》是诗人陈东东沉淀十年之作,书中深度解读了四位有代表性的当代诗人:昌耀、郭路生、骆一禾和张枣。原文刊载于《收获》杂志“明亮的星”专栏,这个出自约翰·济慈的诗句的栏名指向诗人——希望由诗人来讲述如明亮的星一般高悬于诗歌夜空的那些诗人,也希望透过其中的内容,可以给对中国当代诗歌不甚了解的人一个入门指引。作者认为,现代汉诗的归根复命,能够在一个更大的范围里,跟历来的全部(无论古典和西方)文学构筑起共时并存的整体,成为共时并存的这个整体里的传统,而这,正是作者愿意去讲述跟他同时代的一些中国当代诗人的衷心。
.jpg)
大陆的鲁滨逊
中国的当代诗歌,大概启于1966年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尽管,这种当代诗歌写作的苗头,早在“文革”之前就已经破土。流放于高原大山的昌耀(王昌耀),二十八岁时被投入监狱的林昭(彭令昭),二十一岁时写出了《独唱》的黄翔,出没于亚默(伍立宪)“野鸭沙龙”的一些人,上海聚会圈子里的陈建华、郭建勇、王定国,北京“X社”跟“太阳纵队”的郭世英、张鹤慈、张郎郎、牟敦白、郭路生……他们堪称前驱,他们中一些人的写作甚至生命毁于“文革”。而昌耀,以其坚韧持久的创造力,后来成长为当代诗歌里的一位大诗人。
就大概情况而言,不妨把这片大陆上的当代诗人之名,仅仅授予那些“文革”中和“文革”后开始写作的诗人。那就是所谓的“朦胧诗人”、“后朦胧诗人”、“新生代诗人”、“第三代诗人”、“中间代诗人”、“晚生代诗人”,还有“七零后诗人”和现在已经不那么年轻的“八零后诗人”。
.jpg)
在对中国当代诗歌的早期回忆里,总是会提到可以跟鲁宾逊从遇难船上搬往荒岛的有限物资相类比的黄皮书和灰皮书。《局外人》《变形记》《麦田里的守望者》《带星星的火车票》《人·岁月·生活》……这些当年的禁书、“供批判用”的“内部发行”出版物,为当代诗人提供了最初的写作给养。北岛(赵振开)曾提及,这些翻译作品“创造了一种游离于官方话语的独特文体。”在被“抛弃”背景下,当代诗人将游离当作了立足的根据地,进而,开始了“词的流亡”。这正是当代诗人自觉地地下化和边缘化的标志和表现:鲁滨逊转过身去,背对汪洋,到岸上开辟自己的领地。
接下来,一切都是由诗人们自行操办的。当代诗人遵循自己的诗歌理想,确立自己的写作规范和评价标准,并且,打算或已经由自己来刻写自己的文学史墓碑——这种鲁宾逊式的开拓、建功、立业,不只把文明世界从制度律令到生活方式的一整套玩艺儿移植了过来——当代诗人更从“文革”废墟中催生培育了全新的、令现代汉语拔节招展的现代汉诗。
六十年代,那场文化浩劫发动时,昌耀或许正在祁连山深处的劳改农场里构思这诗句;陈建华正在上海弄堂里写着《红坟草》……那场浩劫中,诗人郭世英自杀,诗人张郎郎被通缉,林昭写下的《相信未来》被朋友及知青辗转传抄,流行全国,甚至惊动高层,被江青目作“一个灰色的诗人”。
.jpg)
七十年代,北京地下文艺沙龙和知识青年聚居的河北白洋淀,成为当代诗歌诞生期的重要温床,依群(齐云)、根子(岳重)、北岛、多多,都经常出入于那里;上海的钱玉林、郭建勇、王定国在更早的时候,已经重启了文学聚会;贵阳那边黄翔、哑默及其周边的诗人也在形成新的力量;……他们写下的觉醒之诗,因为要在游离或曰漂泊的境遇里把握自我而转向内在,去探寻灵魂,导致了奥顿所谓的“心的变换”。
到了八十年代,当代诗人开始更自觉地从身体和语言出发写下诗篇,去抵及精神宇宙和大生命之魂。1987年,唐晓渡、王家新编选的《中国当代实验诗选》出版,可以被视为对青年诗歌运动的一种小结。这本书更加注重作为个人的诗人写作的角度去看待青年诗歌运动的观察。这个时期,呈现为“个人写作”的中国当代诗人,北岛、多多、顾城、杨炼、翟永明、欧阳江河、柏桦、王家新、张枣、陈东东、王寅……尽管各有其不同的气质和性情,却都以同一种敬业态度,对待着诗歌写作这件人生的工作。这位鲁滨逊,正在为现代汉诗获得新的自我和自主。
八十年代的诗人们,无论青年诗歌运动中的诗人,还是“个人写作”中更注重诗的自律及生命和精神要素的诗人,都有意识地不让自己的诗歌写作关联政治,更不用说去呼应政治了。或返回自我,或远逸高翔,新的诗歌语言建立在外于政治的另一世界里……然而,正当诗人们以为可以在诗歌写作里自成一统,达成美学自治的时候,现实和诗歌又一次合上了节拍:当政治生活来到一个顶点,诗歌也恰巧处在它周期性的转折点上。
.jpg)
九十年代的诗人们从诗歌写作的炼金术里抬起头来重新打量眼前的现实,包括一向不愿意沾边的政治。此外,还有现实、时代、日常生活里的杂质和历史图景里的乱象,这些“朦胧诗”之后的新诗人在其诗歌写作中有意避开,并不愿与之迎面相向的东西,再次需要诗人们透过诗歌将它们正视。基于此,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当代诗歌显得更为开阔、湍急、相对和浑噩不洁,那诗歌写作的漩涡中心,却留出了魅力无限的呼啸的空穴。真理和绝对悬而不论,诗歌写作不再急欲抵及和触摸它们——大陆上的鲁宾逊要让诗歌朝向无限,让世间万物在一首诗里翻江倒海……
新世纪伊始,汉语诗歌的写作,主要不再是一种书写,而成了在键盘上的敲打;与此同时,诗歌发布的媒体,也转换成了互联网,无须经由审稿、编辑、排版、校对、印刷、装订和递送,就可以一瞬间让无数守在各自显示屏前的读者立即看见。新出现在互联网上的当代诗人,其身份较之以往有很大变化。当文学制度的等级被削平,写作者获得的仿佛无限度的自由发布权,会使之自居为或去成为那种“怎么写都行”的人,他体验着“化名”和“隐身”的快乐,不必文责自负和不妨发挥其恶趣的快乐。
新诗诞生将近百年之际,中国当代诗歌的局面大概是这样的:除了前面提到的那些诗人们许多依然笔力雄健,“七零后诗人”早已登堂入室,“八零后诗人”也已站上了更为广阔的诗歌地平线,被以“中间代”的名义集合起来的那些在过去岁月里诗歌实绩和声名不彰的六十年代出生的诗人,更是一个个走到了聚光灯下。
……
.jpg)
显然,鲁滨逊的故事还没有讲完整——自某个群体的代言人返回个体自身依然不够,现代汉诗必须返回诗歌本身;返回诗歌本身也还不够,现代汉诗还得从它的汉语性、中国性和现代性出发,迈向追认和光大其过去和现在的那个未来。等到造好了大船,他终于要像奥德修斯(更古老的一个鲁滨逊)那样踏上返乡之旅,去找回和融入伟大和悠久。其途径并不确切唯一,其结局也不能预先设定,可以料到的,是他的命运里,仍然少不了持续地漂泊……
(内容编辑整理自《我们时代的诗人》、图片来自网络)